




|
|
干邑被称为生命之水;茶树是南方之嘉木。看似一水一木,远隔万里,但白兰地和茶这两种饮品,其实都是从山野植物中萃取的精灵,是人类将时间和灵魂投入土地而得来的液体,是可赏可啜的古董。 |

|
|
古茶树和台地茶最大的区别是自然生长与人工干预。古茶树并非纯野生茶,也是被先人驯化过的茶树。古茶树在野生状态下是根据自身的环境而成长,肥料养分都来自自然界。而台地茶栽种整齐,培育者会对其进行施肥、除虫、灌溉等护理工作,以此保持茶叶的产量和品质,但这也会影响茶叶自身的品质。 莫干村在景迈山的一处山谷洼里,随地势起伏,傣族吊瓦木楼将整个山谷填满。村边有一座南传佛教的寺庙。寺庙建筑比周边木楼稍高,但并不显突兀。雨势渐大,几个身着黄袍的小僧人撑伞跑向火塘,给这个隐匿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带来几许画意。村中的农人淳朴,见有外人来,都纷纷招呼你进家喝杯烤茶避雨。西双版纳从上世纪80 年代后就成为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但大多数游客都是前往固定的景区景点参观游览,很少前往普洱这一以经济作物为主而不是以旅游为主的地区。这也就保留了像景迈山这样原汁原味的傣族村落。 傣族人饮茶,先把茶叶放入土陶罐中,在火上烤几分钟,再加入热水,待茶水沸腾便可饮用。这种饮茶方式称为“烤茶”。寨子里的老人说,这样的喝茶方式已经延续了上千年,有客自远方来都会用烤茶接待。我们在一家傣族人家避雨,主人用年初刚刚采摘的新茶招待。烹茶中这家老人告诉我,如果早来些日子,就能看到景迈山上祭茶祖的活动。那时,来自各个乡寨的傣族、佤族、布朗族和哈尼族聚集在山坡上载歌载舞。哈尼族那时会唱起一首流传千年的歌曲。 歌词是祖先趴岩冷在临终前训诫后人的话。大意是,“我将离去,留何给后人,牛羊会死,金银会无,留茶最好,世代相传。”古老的茶树被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称做生命之树。杨先生说,景迈山栽种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居住于澜沧江中下游两岸的百越人和百濮人。现在的傣族是百越人的后裔,布朗族、佤族和德昂族是百濮人的后裔。傣族领主曾趴冷岩管理布朗族,如今景迈乡芒景、芒洪及周边的5 个布朗族村寨,村民都认为自己就是趴岩冷的后裔,他们与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起祭祀趴冷岩,并将其尊为种茶的始祖。 只要走进景迈山腹地,古茶树几乎遍布山野。在村中长者和柏联普洱茶庄园茶人的指引下,我在雨后的古茶林中找到了一株年龄已近1200 岁的古茶树。如果是爱茶之人,见到这样的茶树时难免会心生崇敬。它略显老态的身躯上依然在孕育新的叶片,兰花附着在它的躯干上在雨后的阴霾中绽放,空气中弥漫着兰花的香气,这种香气在之前寨子里老人烹茶时的茶汤里我们已经相遇过。此刻我才明白这叶片中所含味道的来源。古茶树边还散落着许多几百年的茶树,这些茶树以最初人们将它们载植在此地的形态自由生长着,没有人工刻意的雕琢排列,而是将一段关于香叶的历史凝固在这里。 |

|
|
大吉岭:喜马拉雅南坡的绿 生命之树的叶片,并非只造福了一方水土,它展开的绿色之路延伸向地球的许多地方。茶树向东传向中原厚土和江南平原,也随着马帮向西进入青藏高原腹地。茶树甚至从海上漂流至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并从那里开始征服了整个地球。 从昆明到印度加尔各答的航程只要3 个多小时。与云南的凉爽相比,加尔各答这座庞大的城市就像是一座无时无刻不在运转的蒸汽机。马路上跑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租车,铁皮巴士和难得一见的人力车从你身边穿梭而过。在号称印度最大的商品市场达克希涅盘,我看到了堆成山的红茶,其中大部分产地都被标示成大吉岭。 此后我曾在尼泊尔、孟加拉国和加尔各答的市场里看到过各种各样标示着来自大吉岭的红茶,但当地熟悉茶叶的人士均告诉我,这些茶多半并不是来自大吉岭地区。茶叶店的老板让他的伙计递给我一杯加入生姜的茶叶,在炎热的夏天喝这种茶叶据说可以防止拉肚子。这也是我和印度茶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后来在印度、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地游历,虽然这些地区的语言是非常难懂的,但有一点不必担心,那就是饮茶。在这些国度,小贩手里提着小型茶炉四处游走,即便你不带任何饮料在身上,只要是口渴时向那些小贩用汉语招呼一声“茶叶”,便可喝到味道极好的奶茶、姜茶或是红茶。茶在这里的称谓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用英语或是本地语代替,而是沿用了汉语茶叶的发音。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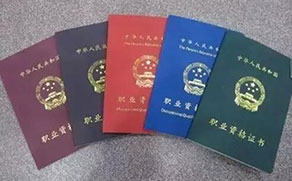
...

...

...

...

...

...